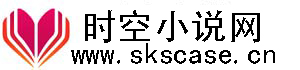70-80(21/31)
之中泛起猩红,埃德温撑起一把伞,罩在已经有能量罩防身的雄虫身上——很遗憾的是, 稀有拯救不了雄虫的脆皮体质,塞拉有幸成为这颗荒芜的边防星球唯一可能被酸雨腐蚀的人形生物。“雌父, 你自己打着。”
塞拉将埃德温手里的伞推回去,即便他知道这种浓度的酸雨连埃德温的头发丝都无法伤害。成年雄虫的身上穿着着一身洁白的礼服,在猩红的天空下格外耀眼明媚, 可是他的肩头却耷拉着,连发顶倔强地小卷毛都萎靡不振。
他不想离开埃德温。昨夜, 他又像个猫头鹰一样守在埃德温床前, 絮絮叨叨地讲着乱七八糟的话——他不得不离开这颗边防星,去处理更紧俏的事,应付迫在眉睫的革命。可是离开埃德温的念头无时不刻不在噬咬他的心, 他无数次想要开口, 说些什么他真正想说的话, 比如以雄虫的身份对埃德温发号施令, 迫使他们不会分离。
或许是他想的太用力了, 他胡言乱语的嗓子说不出话来,像是一口干涩的军用固体营养剂堵在了喉咙里,形成了让人窒息的巨大肿块儿。一直侧躺在床上, 像猫一样安静的埃德温抬起了双眸,无声地看着雄虫,沉默中有什么看不见的丝弦紧绷着,而塞拉漆黑的尾勾从他的尾椎处伸展出来,像毒蛇一样在黑暗中伺机而动。
埃德温仿若未察,连眸光都没有颤动一下。他对着塞拉轻轻张开双臂,松垮的领口露出一片光泽的肌理,起伏之处明暗相撞,在雄虫入怀时瞬间压下了空气中喧嚣的紧绷感。
黑发军雌没有说话,而将棱角分明的俊脸埋入他胸口的雄虫也在双颊升温时无话可说。
他在做对的事,因为他在做埃德温想让他做的事他在给他爱的雌虫自由。塞拉咬牙切齿地想着,用力到让脑海中只留下这一道声音,再也听不见自私的欲望无休止的低喃。他聆听埃德温的心跳,咚咚、咚咚、咚咚,直到那韵律和他的呼吸相合。
“埃德,不要受伤,不要抛下我。”
雄虫的声音变得瓮声瓮气,波本酒味道的信息素在空气中张牙舞爪,无休止的迫近着,绞杀着埃德温原本的气息,可是雄虫的本体却像幼崽一样温顺无害,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姿势埋首雌虫的胸怀中。
“只要一息尚存,我就会回到你身边。”
这是最后一晚埃德温给予的唯一承诺。军雌不擅谎言,而他们都知道在战场上不受伤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,而埃德温从不是惧怕流血而蜷缩在安全堡垒之中的雌虫。
他对得起他肩上的将星,即使这代表他无法兼顾他的幼崽的心愿。
在塞拉看不见的黑暗处,雌虫微微俯首,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塞拉桀骜不驯的卷毛上,手指虚虚穿行其间。有些话没有被宣之于口,但是雌虫的心却坚定不移。
他的雄虫崽走上了一条教廷、乃至皇族为敌的路,这是从古至今都没虫胆敢做的事。但他的虫崽做了,义无反顾,而他们都知道,虫崽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自己。
塞拉是一个力量强大,深受母神喜爱的雄虫,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荣耀和权力,那是别的虫难以企及的,他的能力得天独厚,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置于险境。虫族是一个崇尚力量的种族,他们大多数亲缘断绝,更别提爱情和友谊,塞拉纯粹利他主义的行为在虫族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可是他偏偏这么做了,甚至不惜为一场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的革命,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
为什么呢?许多夜深人静的时候,埃德温都在心里默默问自己。理智上,他知道塞拉所做的一切为雌虫和亚雌带来了珍贵的希望,可是私心总是在寂静时突然侵袭——他反复问自己,为什么塞拉变成了这样